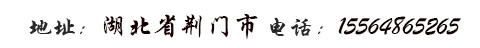试读书院暮春之令三海青拿天鹅
|
北京中医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C%97%E4%BA%AC%E4%B8%AD%E7%A7%91%E7%99%BD%E7%99%9C%E9%A3%8E%E5%8C%BB%E9%99%A2/9728824 内容简介: 和亲的公主去世,女史王徽妍回到阔别八年的中原。 昔日高门的闺秀,如今不仅大龄未婚,还要面对父亲去世、家道中落的窘境。徽妍珍惜与家人团聚的不易,立志拼搏,以一己之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面对昔日暗恋而不得的单身优质竹马司马楷,徽妍心中蠢蠢欲动,不料,身后总有个同样大龄单身的皇帝及时刷存在。 偿债 “债主?”徽妍吃一惊,“什么债主?” 曹谦面有难色,道,“是弘农的债主,主人去年向他借了两万钱,近日天天来要债。” 徽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还要问,曹谦道,“女君,详细之事,小人一个家仆不好多说,女君还是问主人吧。” 曹谦所说的主人,是徽妍的兄长王璟。父亲去世之后,由他掌家。 父亲虽被削爵免职,却还是有家产留下的,这一点,徽妍自己心中有数。弘农的生活定然师比不上长安,但以自家的财力,万万不至于要向人借钱。 疑虑重重,徽妍的心吊起来,到了门前,也顾不得让人通报,直接下车入内。 还未进门,她就听到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 “田公,今日我家中有事,改日再议……” “改不得。王公,你我立契时,约定今年二月偿清,可如今已经四月,加上缗钱,共是两万四千钱。” “两万四千钱!”这是长嫂陈氏的声音,“怎会如此!田荣,你明知晓这钱并非我家所借!” “确非王公所借,可陶绅如今不知去向,借契上写得明白,王公师保人,在下不向王公讨要,向谁讨要?” 王璟气急,正要怒斥,忽而见徽妍走了进来,面色一变。 “出了何事?”徽妍冷冷地看着那个叫田荣的人,“足下何人?” 她做女官多年,虽一身布衣,亦自有威仪,田荣被她逼视,一时竟有些愕然。 徽妍审视着这田荣,只见生得方面大耳,眼小如鼠,身上虽锦衣金带,却活脱的俗气,不掩奸相。 “徽妍……”王璟神色不定,顾不得见礼,忙对陈氏道,“你先引徽妍去见母亲。” 陈氏明了,缓和了神色,对徽妍道,“小姑一路劳顿,且随我入内……” “长嫂且慢。”徽妍却拉住她,再转向田荣,“足下说我家签你钱,可有借契?” 田荣打量着她,笑了笑,“原来是王女君。在下敢来要债,自有借契。” “还请一观。” “一观?女君莫非要还钱?” 徽妍不答,却道,“足下来讨债,莫非不带借契?” 田荣犹豫片刻,让从人将一块木牍拿出来,呈在徽妍面前让她看,但不许碰。 徽妍看去,只见上面写着,一个叫陶绅的人向田荣借债两万钱,为期一年,缗钱什二。落款处有陶绅的名字和指印,保人王璟的名字,也有指印。徽妍看着,心中一沉。 “徽妍,”王璟忙解释道,“这些钱是为友人借的,但他不见了踪影……” “兄长,那字迹与指印,确实是你的么?”徽妍问。 王璟面有愧色,颔首,“正是。” 徽妍心底叹口气,对曹谦道,“曹掌事,我行囊之中,有些财物。去取这契上的数来,还与债主。” 曹谦忙答应,匆匆走开。 田荣听得此言,惊讶不已,笑逐颜开,向徽妍作揖道,“小人早知府上明理!多谢女君!” 徽妍不与他多说,待曹谦取来钱物,只见都是*澄澄的金子,足有 斤。徽妍看着曹谦称量分割,交与田荣清点,无误之后,道,“借契还请还来。” 田荣忙不迭地让从人将借契奉上。 徽妍收了,转向兄嫂。 二人神色复杂,王璟十分过意不去,“徽妍……” 徽妍微笑:“兄长不必多说,母亲他们在何处?” 这处家宅是徽妍的父亲亲自定下的造式,有前庭、前堂、几处宅院以及后园,工匠都是京城过来的,用料做工皆上乘。 晚风徐徐,带来庭院中月季的香味。徽妍跟着兄嫂来到母亲戚氏的宅院中,只见屋里已经亮了灯,传来小童欢笑之声。 戚氏今年五十多岁,正在后宅教女儿用织机,三个孙子孙女则在房中玩耍,十分热闹。见徽妍回来,戚氏高兴不已,却又老泪纵横,抱着她大哭一场,众人劝解一方才罢住。 “怎这么慢?”她埋怨道,“家人早来报你已到陕县地界,你兄嫂说要迎你,出去了许久不见回来,我差点等不及要去看。” 王璟夫妇脸上有些尴尬,徽妍忙道,“是我路上耽搁了些,母亲,如今不是到了?” 戚氏露出笑容。母女分离了八年,戚氏拉着徽妍的手不肯放,看着她,似乎怎么也看不够,问她路上如何,在匈奴可曾受人欺负。 徽妍依偎在母亲怀里,亦是许久未有的温暖,擦着眼泪一一答来。 “八年,简直似做梦一般。”戚氏说着,眼圈又发红,“想你当年离开时,不过萦一般年纪,如今你归来,萦已经长大,母亲亦两鬓苍苍。徽妍,母亲总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,你父亲去时,亦总念着你……” 说到难过之处,众人又垂泪。 徽妍的妹妹王萦今年已经十五,虽稚气未脱,却已是亭亭玉立。对于徽妍,她只有些约摸的印象,如今相聚,她望着这位姐姐,眼里更多的是好奇。弟弟王恒,如今却不在弘农,母亲告诉她,王恒到雒阳求学去了。 就算父亲去世,王恒不在,这仍然是一个热闹的家庭。王璟夫妇,生育了两男一女,大的八岁,中间的五岁,最小的才三岁。一番倾诉之后,徽妍取来将自己在长安置办的礼物,送给家人。众人皆是欢喜,孩子们得了玩具,高兴不已。王萦儿时离开长安,对那里也已经不太熟悉了,看着姊姊送给她的物件,爱不释手。 看着众人喜气洋洋,徽妍心中亦是满足。此情此景,若在几个月前,她简直想都不敢想。 戚氏拉着她,让她说在匈奴的事,徽妍说起阏氏和她的儿女们,还有匈奴的风俗。众人听故事一般,津津有味。 “瑜主这般坚强女子,竟早早离世,实为可惜。”戚氏叹道。 陈氏笑着小声道:“姑君莫忘了,若非如此,小姑如何归汉?” 戚氏恍然了悟,忙道,“正是正是,老妇真糊涂了!” 徽妍在母亲房中一直待到夜深时分,直到哄了母亲睡去,才起身离开。 才出房门,却见王璟立在外面。 “徽妍,”面带愧色,低低道,“难为你了。” 徽妍知道他还放不下那借债的事,忙道,“兄长不必挂心。” “徽妍,你不知晓。”王璟叹口气,“今日若非你,此事只怕无法收拾。”他停了停,道,“徽妍,家中已经无多少钱财可用了。” 饶是已经有了些准备,听到这话,徽妍还是吸了一口凉气。 徽妍先前的想法没错,王兆去世时,确实留下了些家财。一家人回到弘农之后,也过了几年殷实的日子,吃用不愁。徽妍的母亲年迈,管不了许多事,家中全由王璟夫妇当家。 王璟继承了父亲的性情,宽厚通达,而妻子陈氏亦是长安富贵之家长大,温柔贤良。夫妻二人掌家,伺候母亲,照顾弟妹和儿女,俱是周到。且待人和气,亲戚友人有求而来,必慷慨相助。 近几年,弘农的年景不太好,尤其前两年,遭过一次大蝗灾,颗粒无收。徽妍的父母兄嫂,过惯了长安的日子,生活开销一直不小。来到弘农之后,虽已经有意节省,但偌大一个家,光仆婢就有三十几人,支出仍是大数。可他们已经没有了朝廷的俸禄,而父亲留下的田产,并不足以支撑这些。所以,家里一直在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,以至于家中余财日渐消耗,捉襟见肘。 而今日之事,因由乃在去年。王兆从前有一位同乡,叫陶绅。此人曾到长安家中做过几回客,王璟认得。去年,陶绅从长安来,说自己的家宅在大乱时被毁坏,一家人没了着落,只得与弘农的田荣举债。可田荣说他无资财可抵,不肯借,所以他只能来求王璟为他做保人。王璟觉得此人是家中旧识,当不会有诈,便应承了此事。不料,一年过去,债主来要债,去寻陶绅,却怎么也寻不到了。债主紧逼,而家中钱财都借了出去,这两年维持上下生活,库中的余财也所剩无几,王璟若要还债,只得变卖那点田地。 “陶绅说,他在扶风还有田产,只是来不及处置。他得了钱安置了家人,便将田产典卖,得了钱就还我。”王璟说罢,苦笑,“徽妍,父亲将家交与我,实为下策。你知晓的,我只会读书。” 徽妍听着,只觉太阳穴隐隐发胀,也只得苦笑。 王璟说得没错。自己的兄长,如何性情,她是知道的。 “兄长所欠债务,除了这个田荣,还有别处么?”徽妍问。 “没有。”王璟忙道。 徽妍松一口气,再问,“这些事,母亲知道多少?” 王璟道:“母亲身体不好,我不敢禀报许多。” 徽妍心中有了数,颔首,“如此,我知晓了。” “你欲如何?”王璟有些犹疑,“徽妍,你若是要去求诸位叔伯相助,大可不必,我见他们并非好相与之人。家中也并非十分艰难,实在不行,将奴婢卖去些也好。” “兄长且宽心。”徽妍笑笑,“我可是从匈奴归来的女史。” 家宴 徽妍回了家来,第二日起身,便去拜祭了父亲。 王兆的墓,就在离家不远的一处树林里,旁边种满了他最喜欢的竹子,鸟鸣声声。 徽妍眼圈红红,将一碗父亲 的梅子酒洒在墓前,看着碑上的字,忍不住哭泣起来。 戚氏将她拥在怀里,哽咽道,“你父亲常说,此生 的憾事,便是再见不到你。如今你给他敬了这酒,他便也安心了。” 徽妍伏在她的肩上,许久,点点头。 王家许久没有操办过喜事,如今徽妍回家,众人皆是高兴。为了给徽妍接风,戚氏令王璟设宴,派仆人到各家亲戚那里通报,邀他们到府里来聚宴。 日子就在明日,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,杀牲的杀牲,置办的置办,到处是忙碌的仆婢。 徽妍却一直待在屋里。 她找到曹谦,向他要来账册,想将家底摸索得清楚些。 账册上写得十分明白,父亲留下的财产,除了这屋宅,另外就是二十顷地。父亲是个喜好风雅的人,当年买地,全然 风景优美之处,故而这田庄四周,有桑竹环抱,溪水点缀,小丘如画, 的缺点是土质不佳。曹谦告诉徽妍,因得如此,就算在稍好的年景,佃户交来的租收也并不可观。 徽妍在册上看到,他们家迁回弘农以来, 一笔开销是刚来的时候修葺屋宅。此间的房屋闲置多年,要重新整修,王璟为了让家人住得舒服些,在此事上花了十万钱。其余开销,与之相比并不算大,但积少成多,加起来也是大数。 她还看到一些借出去的钱,名目上写的是各家叔伯亲戚,少则一二千,多则上万,不禁皱了皱眉。 “叔伯们也来借钱么?”她问。 “借过。”曹谦道,“前两年蝗灾时,弘农物价涨得狠,时常有叔伯亲戚说无钱可用,上门来借些。” “可有借契?” “无。”曹谦苦笑,“女君,你知晓知道主人为人,那都是至亲……” 呵呵,至亲。 徽妍在心中冷笑,不说话。 她们家可能有些穷亲戚,但绝不是这些叔伯。 当年徽妍还在长安的时候,他的祖父就已经去世了。王兆当时任太子太傅,过得最是富贵,为人也慷慨。分家时,王兆只要了些父母不值钱的遗物做念想,其余全由四个兄弟们处置。 所以在弘农虽是他们一家人的故乡,王兆却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任何田产。如今传给儿女们的田宅,都是他自己出钱另购的。据她所知,几位叔伯分到的田地,最少也有十顷,且都是良田,说不定如今家境比王璟这边还好。 徽妍看完,感到事态严峻。 她这些年攒下了些钱财,朝廷的赏赐之物也算丰厚,用来支撑家里的生活倒不是难事。可若是仍然这般过下去,只怕多少钱财也迟早会用尽。 徽妍闭了闭眼睛,觉得心烦意乱。 “二姊?”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,徽妍睁眼,只见是妹妹王萦。 她梳着总角,手里捧着一只食盒。 “萦,你怎来了?”徽妍打起精神,坐起来。 “庖厨中刚做了米糕,我想你应该也饿了,带些来给你。”王萦说着,打开食盒。 徽妍看去,只见里面果然盛着些新鲜的米糕,还冒着热气,不禁莞尔。 “你还记得?”她轻声道。 “我不记得谁还会记得?”王萦得意地说,眼睛亮晶晶的。 ……从前在宫学,卿不是每隔两个时辰就要去御膳中讨小食? 不知为何,徽妍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听到的那句相似的话,不禁愣了愣。 “吃吧。”王萦拿起一块米糕,塞到她手里。 徽妍咬一口,温香软糯,不禁心满意足。 说来,她和这个妹妹,从前一直很亲密。徽妍大王萦九岁,王萦识字都是徽妍教的。在长安的时候,徽妍无论做什么,王萦都喜欢跟在她后面,包括时不时去庖厨觅食。徽妍曾经觉得照顾她很烦,常常躲开她,自己去玩。但是到了匈奴之后,她又时常怀念王萦眼巴巴跟在自己后面的样子,后悔自己不珍惜。 她把王萦拉到身旁,一起吃米糕。 “你平日在家做什么?”徽妍问。 “看书。”王萦说。 “真的?” “假的。”王萦吐吐舌头,小声道,“我会关上门,翻窗出去玩,二姊,你千万莫告诉兄长。” 徽妍笑起来,抱了抱她。 “二姊,”王萦埋头在她怀里,低低地说,“你不会再走了,是么?” “不会了。”徽妍抚着她的头,“我再不会离开你们。” 举办宴席的当日,宾客盈门。 来的都是父母两边的亲戚,徽妍大多不认识,只能跟在母亲后面,听着家人传报,微笑一一行礼。 四位叔伯也来了,各自带着家人,有一大群。 “这是徽妍?”大伯父王和六十多岁,身体胖得几乎腰带都要勒不住,笑起来眼睛都几乎不见,“回来甚好!从匈奴回来,可喜可贺!” 徽妍行礼:“多谢伯父。” 二伯父王佑,四叔父王叙,五叔父王启也来相贺,人人皆是福相。 伯母和叔母们则围着戚氏说话,你一言我一语。 “徽妍去了匈奴回来,长得都快认不出了!” “听说匈奴风水伤人,依我看也未必,徽妍可是越长越好。” “你这话说的,徽妍小时候在长安,你见过么?” “那时确是见不到!徽妍可是宫学中的侍读,我等平头百姓岂可轻易见到,呵呵呵……” 说了好一阵,亲戚们才去堂上,在席间坐下。 “长姊怎还不来?”王萦来到堂前,踮着脚不住往外望。 徽妍亦是此想,问曹谦,“长姊那边可派了人去告知?” “告知了,”曹谦道,“大女君还说一定要来。” 话音才落,大门外忽而出现了两个身影,徽妍定睛看去,不禁露出笑容,那正是她的长姊王缪和姊夫周浚。 王缪排行第二,大徽妍六岁,如今虽已经年近三十,却仍面容娇美,走进门,似门庭生光。 徽妍和王萦忙迎上去,与二人见礼。王缪将她扶起,端详片刻,微笑,“长大了,可不是小女儿了。” 话语虽短,徽妍听着,心中却是一酸。 从前在家中,长姊就总说她是“小女儿”,姊妹两人藉此拌嘴,一直拌到王缪出嫁。徽妍去匈奴之后,姊妹二人八年不曾相见,也不曾通信,如今见面,心事澎湃。徽妍望着姊姊,那张脸虽未改,笑起来却已经有了些淡淡的纹路。她握着王缪的手,说不出话来。 周浚在一旁见状,拉拉王缪,笑道,“莫小女儿长小女儿短了,如今的小女儿不是萦么?” 王萦愣了一下,笑嘻嘻地说,“姊夫此言在理,小女儿是我!” 徽妍和王缪破涕为笑。姊妹三人相携,一道上堂。拜见了母亲和亲戚们之后,又一道入席。 宴上宾客实在太多,聒噪不已。不过徽妍在匈奴做女史的时候,经历过胡人们聒噪百倍的宴席,倒是不以为意。 用过膳后,男子聚在一起饮酒,女眷在坐在一处聊天。未成年的儿女们到处奔跑玩耍,吵吵闹闹。 “徽妍到底是女流!”男人那边不知说到了什么,一个堂兄醉醺醺地站起来说,“我若是你,伺机一刀斩了单于,扫除边患,陛下定然封我做个万户侯!” “莫瞎吹!你尚书也背不下几篇,做得女史么!” 众人哄堂大笑。 “徽妍今年,可有二十五了?”一位伯母问。 “刚满二十四。”徽妍道。 “不小了,”那位伯母语重心长,对戚氏道,“如今既然回来,还是尽早婚配才是。” “可不是。”一位叔母吃着果子,“要我说,当初就不该送去做什么女史,还不如我等生在乡间的女儿,早早成家。” 王萦听到这话,脸色变了变,看向徽妍。 徽妍却似未闻,笑笑,没有答话。 众人你一眼我一语,王缪见徽妍不语,道,“去年兄长在后园中新载了好些花树,不知如何了?” 徽妍知她心意,道,“我带姊姊去看。” 说罢,姊妹二人起身,往后园而去。 午后,微风轻抚,园中只有小童们玩闹,二人赏花散步,终于能喘口气。 “你莫怪那些人,他们每日无聊得紧,好容易得了机会开开口,岂有放过的。”到了花园里,王缪开解道,“些许蠢话,你莫往心里去。” 徽妍莞尔:“我知晓。” 王缪道:“是了,有一事要告知你。你姊夫提了官,入大司农的平准府,我等年初时已经搬去了长安。可惜几日前你不知晓,不然可住到我家里。” “哦?”徽妍眼睛亮了亮。 王缪的丈夫周浚,出身沛县周氏,是个世家子弟,祖上是功臣周勃。周浚的父亲,也曾在长安太学做学官,因而与王兆交好。王兆升任太傅之后,周浚的父亲上门来为儿子求娶王缪,王兆答应,便结了亲。周浚是个才能不错的人,对人亲切,徽妍其实挺喜欢他。他在雒阳为府吏,管市中赋税,来家中做客时,常给徽妍说市中商贾的事情,说得精彩绝伦,徽妍觉得十分有意思。他此番升官去了长安,徽妍是真心替他高兴。 据徽妍所见,周浚和王缪婚后一直恩爱,美中不足的是,王缪连生了两个都是女儿。在徽妍去匈奴之前,王缪又怀了第三个,后来在兄长的来信中得知,仍然是个女儿。 “周家的舅姑待你如何?”徽妍问,“还总说你不生孙儿么?” “还能如何?生什么又不是我想便有的。”王缪道,说着,撇撇嘴,“父亲那事之后,许多亲热的故人都不见来往了,那边待我已经算仁善。” 徽妍听出了王缪话语中的怨气,愣了愣。 王缪四下里看了看,淡淡道,“徽妍,父亲去世前,曾为萦定过亲事,你知道么?” “亲事?”徽妍惊讶。 王缪看她神色,颔首,“想来兄长纯善,不会与你碎语。定亲的是奉常何建的孙子,可父亲罢职之后,那边就把婚事退了。”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baishaoa.com/bsyl/510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药入门补血药白芍
- 下一篇文章: 岳美中简谈内伤发热的治疗